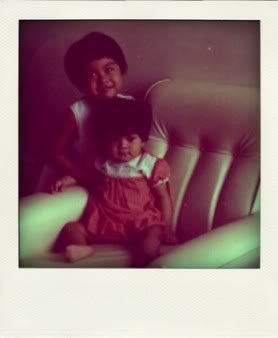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七篇林奕華
>>>Saturday, May 10, 2003
有些題目是永遠談不完的,像「甚麼是『鍾意』?甚麼是『愛』?」繼而眾口一詞﹕「憑感覺呀﹗」。然而尾隨的不是句號,卻是另一個問號﹕「為甚麼許多時候,開始叫『愛』,中途叫『冇感覺』,最後變成『唔鍾意』?況且對象是同一人﹗」結論,回到老生常談﹕「甚麼叫『感覺』?」恍如追蹤颶風質問﹕「早知不會懸掛八號風球,幹嘛又要給我們(最好各種心理準備的)三號?」
「愛情」已經離開「個人感受」很遠了—當大家面對「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而甚少懂得找尋答案的樂趣之際,我們又怎能期望不同的人能夠帶來不同的情感素質—它,體積雖大,但是大而無當,因為「它」不下於深入民間的兩家電視台,專為我們生產包裝不同,內容卻千篇一律的現成貨色。
甚至連虎頭蛇尾的架式都像得很—電視劇不是通常都只有頭三、五集好看嗎?電視台為了吸引觀眾而在開篇落重本錢,就像許多愛情關係捱不住時間的考驗。
「鍾意」,有若路經一家餐館,被它的裝潢和氣氛懾住,原來食物也不錯,於是光顧上一次又一次。及後遇上也合心水的另一家,自然便不上門了。
「愛」是上菜場把食物買回家去自己煮—戰戰兢兢有之,多番練習而改善有之,功敗垂成亦無不可,分別在於「過程」之中,以試驗為主,所以「感覺」才會從無到有。
林奕華﹕〈試驗〉,《Edward Lam On Love》(香港﹕陳米記,2002),頁 22。
用眼睛去「鍾意」一個人—很好呀,可以鍾意他或她的笑容、眉毛、酒渦、髮型。或者,木訥、酷、兇神惡煞。「視覺」作主,可以讓我們看見前所未有的美好(相反者,便是不為所動),於是左腦告訴右腦﹕「你戀愛了﹗」
「鍾意」和「愛」本無必要互相排斥,即是,你愛的某人,同時是你鍾意的某人—除了看,還不要忘記「如何看」。
甲被乙的笑靨懾住,而丙反問﹕「為何他只看見對方的笑容,馬上便說鍾意,因為『她很開朗』?」丙說﹕「現在的人們『看人』,為什麼都那麼片面?」
另一說法,是信念全數押在自己所喜愛的一點上,其他景觀,任它濛成一團。當然,「看」能夠帶來即時的愉悅和快感,相比起來,「如何看」卻要用上更久的時間,更多的心機,兼且矛盾經常發生,像,這麼漂亮的一張臉,怎會作出這樣不堪的行徑?屆時,兩難局面勢必把當事人拉成拔河用的一條繩。
鍾意他或她,何不更加仔細的「看」?看這個人如何對待大小的動物,如何承受突如其來的打擊,如何面向榮譽和讚賞,如何接受事與願違的現實,如何在一桌引不起他或她任何食慾的飯菜前舉起筷子,如何處理自己的情感和幻想。
「看」的角度愈多,「鍾意」才不會變成飄浮半空的肥皂泡,隨時破滅。
〈鍾意〉,同上,頁 23。
深夜,我跟電話另一頭的好友說﹕「都為了我們重視自己多過我們認為所愛的那個人吧,而碰上他也如此,或,他亦只能如此。」語調中不無一點的感觸,蒼涼,皆因這是很多現代人的共通點,我和好友又豈能例外?
追求情感生活,與學問不遑多讓,都是不進則退。唯是兩者的差別,在於情感的深淺,不能盡由單方面來自決。陳腔濫調必有其真理﹕「兩個人才跳得成探戈」,可見步伐的協調,才是相處的真諦。假若舞步出了亂子,你堅持不收回一步,他又拒絕踏出另一步,那只是丟人現眼的進退失據,不能叫探戈。
我們心目中最美滿的愛情,少不免是以自己為主角—他或她的存在,應該是以烘托我的夢想與理想為前提。雖然也有紆尊降貴的時刻—你既敬我一丈,我就用一尺回報吧—那份牡丹客串綠葉的委屈,只是變相地把籌碼貯存起來,留待日後才套現。
這樣驕縱的我們,只能等候甚麼都不計較的一個人。但,果真有求必應,我們又有何得著?可以證明自己百份百地被愛,難道就能補償不懂自我要求的損失?美其名想要被愛,多少多少的捶胸頓足,不過是爭取被寵的表現。
這時候,認識自我比了解對方如何更為急切—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然而自己的淤血積塞,則失戀將以歷史之名重複自己。
〈重複〉,同上,頁 26。
俗云「愛情總是自私的」,乍聽玄之又玄,何不把話說得直接一點﹕(所謂)愛情,可以只是追求 good time。而「好時光」的一般定義,乃事事根據自己的意旨而行,最好連太陽都是為了看我才升起。
唯有滿心愜意,時間才會飛逝,做人才不是逆水或陸上行舟。有人相信「對自己好比甚麼都重要」,於是把字面的意思,當宗教般膜拜,尤其「自己」—你若愛我,就該以我所選擇的方式來待我,好讓我做自己的主人;你呢?或許是客,或僕人。
跟從這種規則的,不論是兩個或三四五個人,最後,其實只有一個—追住自己的尾巴團團轉,完全出於這個「我」的盲點﹕只知道接受的好處,卻不明白付出才是所有愛情的種子。
縱然在他或她的觀點之中,花了金錢,貼上時間,已是莫大的捐獻,因為同樣的精力,大可留來「給予」另一個人。分分秒秒以回報計算,當然不會把目光放遠,或,目光只是被這個「我」用來物色更有狩獵價值的下一個目標。
矛盾在於,獵人有時竟也在自設的陷阱裡受傷、嗚咽﹕這樣奔波、勞碌,為何還是一日比一日寂寞、孤獨?一張臉從鏡子反映出來﹕塵滿臉,鬢如霜﹗
愛情的有與沒有,也許不在如何選那最好的,而是怎樣聚焦。
〈聚焦〉,同上,頁 30。
甚麼是聚焦?容許我打一個比方﹕買一本書,把它從第一頁至最後一頁好好讀完,順不順序是其次,緊要的是,讀它,而不是買它。
或,為了拋棄而擁有。
然而,喜歡收購多過實際應用(一本書、或VCD、衣服、一個人)的我們,總會找到自圓其說的藉口—「現在不買就會漲價了、絕版了、回收了」—腰包被掏得一窮二白之餘,本人也莫名地貧乏起來﹕「噫,不是擁有了半間『葉壹堂』和HMV麼,怎麼生活仍然百無聊賴,死水一池?」(感情生活亦如是)
買,不一定等於貪婪。我可以未讀過《追憶逝水年華》,但一聽有本叫《How Proust Can Save Your Life》的書,馬上搜尋它的下落。這有點像用慣電腦而得了後遺症:數個介面同時佔據一個屏幕,方便我們喜歡哪個,便往哪個click去。而,「後遺」也不一定解作壞影響—假如它真能幫助你更靈活地讀完一本書、認識一個人。
只不過,更多人屬於「兩套書都擁有」,繼而漫無目的地跳著看、掀著看,看了頭兩章就不看,總之,提不起勁,對不了焦。
焦點者,目的也—為何我們先說想看(書),所以才買,買了才發覺不想看,但是出此語的一刻,另一本又已拈上手,隨時準備結帳?搞不清楚目的「目的」,可是為了成全「有殺錯,冇放過」?
〈目的〉,同上,頁 31。
過去,不一定展覽在一個人的臉上,所以,一個人的過去,不比時下流下的網址,不可能被選擇性地瀏覽,只能像錄影機發明之前的電視劇般,一集一集地,考驗我們是否有耐性和毅力定時收看。
難怪許些愛情都在由淺入深的階段,畫面忽然中斷或跳台。愛人的過去,可以是愛情的試煉,利用對象的歷史來替這段關係評分,沒有錯,控制權穩操在手,繼續愛或不愛,都不致影響愛人的安全感。相反的,便是接受所謂不利的位置:被動。
不利者,即是結局沒法預計─來龍去脈清楚了,不難使我們向了解踏出嘗試的一步。但是,從了解提升至接受,或從不接受到重新考慮何謂接受,太多事情不能由一己的信念包辦—假如對方根本沒有打算面對過去,「愛人」又能怎樣?
一樣的看戲、吃飯,同時明知他或她的笑容裡沒有了一點很重要的甚麼。你有試過在談戀愛之際,猶如置身網上的聊天室─心神恍惚於片言絮語?
不愛自己,所以才找尋一個愛自己的人,然而當這個人出現了,又嫌他或她把自己帶回問題的起點:「我」是誰?「我」不是為了要把這個忘記,才談戀愛的嗎?
不與愛人分擔過去,不代表過去不在影響著兩個人─這樣的愛情,是只讓一個人有決定將來的權力,是自私的鼓吹。
〈將來〉,同上,頁 37。
I am what I eat. I am what I wear. 容許我杜撰一項:沒有「我」,根本不會有我的愛人─「愛人」,很多時候是由我們的性格所塑造的。可見遇上怎樣的人,並不是愛情最大的關鍵,「我」是怎樣的人,才真的計數。
遇人不淑的故事多的很,但是我們不應繼續以「怒沉百寶箱」為借鏡─如果要靠金銀財帛才能使變了心的人悔不當初,你不過是教曉他愛物,而不是愛人。
杜十娘的教訓被引用至今天,可見在「愛情」這題目上,大家還是十分害怕看清楚自己─譬如,當事人的被騙,難道真是百份百在被蒙蔽之下進行?抑或從一開始,她便是以物質來吸引她所追求的對象,直至情況失控,才不得不揭開自己的面紗?
愛一個人,是要用自己的性格去愛的。我的意思是,假若我們明白到自己不了解自己,沒有耐性,又經常自圓其說,自欺欺人,我們就得接受失敗的不斷重複,因為那是力量的不逮,或者可以稱為性格所限,不得怨天尤人。
撇開對自己的要求不談,就是別人要愛或不愛上我們,性格也會佔上決定性的分數呀─如果他或她也有能力知道甚麼叫做「性格」的話。
你叫我隨隨便便地吃和喝,可以;但是做人,性格必須行先。同樣,和一個我不了解的人尋歡作樂也可以,但那不叫戀愛。
〈性格〉,同上,頁 46。
:: posted by my lock, 6:42 A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