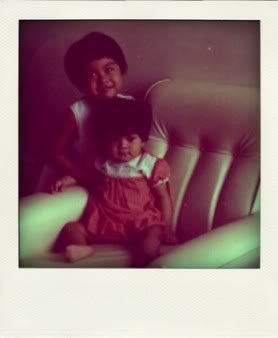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in the name of ...
>>>Friday, September 29, 2006
 記得以前上新詩創作課,老師講過幾個寫作的條件。我大概真的不是個好學生,不能把五個答案牢記在心頭。只知其中之一的恆心(persistence),是我所嚴重欠缺的。而唯一能夠受之無愧的一項,大概就是敏感(sensitivity)了。有時甚至到達一個隨時被認為是妄想病患(paranoia)的程度。
記得以前上新詩創作課,老師講過幾個寫作的條件。我大概真的不是個好學生,不能把五個答案牢記在心頭。只知其中之一的恆心(persistence),是我所嚴重欠缺的。而唯一能夠受之無愧的一項,大概就是敏感(sensitivity)了。有時甚至到達一個隨時被認為是妄想病患(paranoia)的程度。但他如此強調敏感,並隨便舉例如同拾起身邊的鑰匙﹕讀到報紙雜誌上印有自己喜歡的人的名字的其中一個字,即使散見和零碎,都會隱隱揪著心,牽繫著凌亂的思緒。
那個時刻,偌大的講堂上一室通明,大概並非一個適合感觸的環境,但我仍然打了寒噤,差點溢出卑微的淚。像他在從前寫的文章中提起的微遠燈火,千萬人中,有多少個會同樣注意到黯紅的神檯燭火呢?又當他聽到別人在未有聽過〈陳大文〉,就妄下判斷的時候,氣氛也突然變得緊張了。
再喊那個人的名字,像落入荒原,被黑洞吞沒,連嘆氣都不再精緻。擁有這種極致的敏感會快樂嗎?我常常渴望自己可以無知無覺,無視感受,相信看見的真相,相信耳朵與謊言。但我做不到,無法撲滅心頭那束光。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頭仍皺滿密雲。就算一窩暗燈,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如果我可以換一層皮膚,就不用被目為煩惱自尋的煩人了。有利寫字的,卻往往窒礙甜美生活。今天我需要的只是愛。
一席課後,我再次肯定,最愛原是流行歌詞。然而,這麼近那麼遠,即使我們同處一架昇降機,十多年的戀慕又要如何表達呢?像他又再提起的張小姐的名言﹕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我站在你跟前,而你不知道我愛你。
* 2006/10/10
:: posted by my lock, 9:58 P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