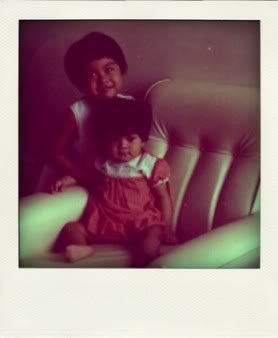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I/M
>>>Sunday, April 16, 2006
我們在一隻匣子之中聆聽另一隻小盒子所發出的聲音。為了耳畔的溫柔,我其實真的很想哭,就像他掠過我的身邊,翻起一陣很冷的風。然而我禁不住對她微笑了。原來也有些驕傲,不全然為了我自己。那可以稱為愛嗎?
我給她沖了一杯咖啡,小匣子成為我倆偷閒的天地。但今夜我們竟然聊到死亡的可怖。她問我有沒有讀到那樁行山人士摔死的新聞?原來不幸者是她的鄰班同學,縱然只是點頭之交,但我們竟慢慢嗅到死亡的氣味。像不久之前,我也到過靈堂,流過一點眼淚。消失,或者比我們想像都更容易。
幸而這一刻,我們存活。到白木屋吃喝,閒談間我知道她不認為那足以構成傷害。也許彼此的情份太少,少得,他甚至不會感到癢,更不言傷害。苦惱的只是我。我無法不吞下當中的不屑,也未能理清自己的慾望。當中的落差叫彼此跌入一種互相敵視的情態之中,然而我不想憎恨我喜歡的人,縱然他一點都感受不到。我如此深切地體會到溝通的無力。
放棄語言吧,我想。我不明白角力和周旋。我嚮往的事物簡單和原始得叫人害怕。像那個還沒有出名的小歌女在這個通宵達旦的購物商場表演唱歌和跳舞。而她狠狠的說,那女子不過賣弄她的身體。但即使她真的販賣她那青春的胴體,又有甚麼值得羞恥?我就是喜歡身體的直接。如果沒有身體的觸碰,我如何抓住說謊的憑據?像某些精於捕捉語言的人,一層又一層無法撕開的包裝,觸痛了我的神經。當然身體的反應也不見得不能偽裝,但相對複雜的語言,那不由自主讓我記得,我們是人。

正如午夜看的那齣電影,為甚麼偏偏要安排父女上床的錯摸?曾幾何時,我患有嚴重的戀父癖,儘把喜歡的男人都叫做爸爸。我不知道那些人真正的感受,只知道他們複雜的神情──有時源為了一個擁抱。於是我就很喜歡她與他因為酒醉而在街上胡鬧的一段,多麼真摯,最後即使躺在床上,也可以很簡單。鏡頭最後捕捉杜汶澤微濕的汗衫,讓我的眼淚無法抑止。那種細摯,叫人實在地感受到那份說不出的情感──怪不得她願意跟我再看一次,這齣會喚起我瑪格烈特的電影。
(偶然會想起那年為了看《河流》而借用朋友學生證潛入城大圖書館,如何不理會在那隻冰冷發白的箱子中往來的人們,而尷尬看父子亂倫的片段。我曾經有過的熱情,難道都燃燒殆盡了嗎?瑪格烈特比我懂得何謂快樂,何謂不滅的愛。)
我給她沖了一杯咖啡,小匣子成為我倆偷閒的天地。但今夜我們竟然聊到死亡的可怖。她問我有沒有讀到那樁行山人士摔死的新聞?原來不幸者是她的鄰班同學,縱然只是點頭之交,但我們竟慢慢嗅到死亡的氣味。像不久之前,我也到過靈堂,流過一點眼淚。消失,或者比我們想像都更容易。
幸而這一刻,我們存活。到白木屋吃喝,閒談間我知道她不認為那足以構成傷害。也許彼此的情份太少,少得,他甚至不會感到癢,更不言傷害。苦惱的只是我。我無法不吞下當中的不屑,也未能理清自己的慾望。當中的落差叫彼此跌入一種互相敵視的情態之中,然而我不想憎恨我喜歡的人,縱然他一點都感受不到。我如此深切地體會到溝通的無力。
放棄語言吧,我想。我不明白角力和周旋。我嚮往的事物簡單和原始得叫人害怕。像那個還沒有出名的小歌女在這個通宵達旦的購物商場表演唱歌和跳舞。而她狠狠的說,那女子不過賣弄她的身體。但即使她真的販賣她那青春的胴體,又有甚麼值得羞恥?我就是喜歡身體的直接。如果沒有身體的觸碰,我如何抓住說謊的憑據?像某些精於捕捉語言的人,一層又一層無法撕開的包裝,觸痛了我的神經。當然身體的反應也不見得不能偽裝,但相對複雜的語言,那不由自主讓我記得,我們是人。

正如午夜看的那齣電影,為甚麼偏偏要安排父女上床的錯摸?曾幾何時,我患有嚴重的戀父癖,儘把喜歡的男人都叫做爸爸。我不知道那些人真正的感受,只知道他們複雜的神情──有時源為了一個擁抱。於是我就很喜歡她與他因為酒醉而在街上胡鬧的一段,多麼真摯,最後即使躺在床上,也可以很簡單。鏡頭最後捕捉杜汶澤微濕的汗衫,讓我的眼淚無法抑止。那種細摯,叫人實在地感受到那份說不出的情感──怪不得她願意跟我再看一次,這齣會喚起我瑪格烈特的電影。
(偶然會想起那年為了看《河流》而借用朋友學生證潛入城大圖書館,如何不理會在那隻冰冷發白的箱子中往來的人們,而尷尬看父子亂倫的片段。我曾經有過的熱情,難道都燃燒殆盡了嗎?瑪格烈特比我懂得何謂快樂,何謂不滅的愛。)
:: posted by my lock, 5:34 P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