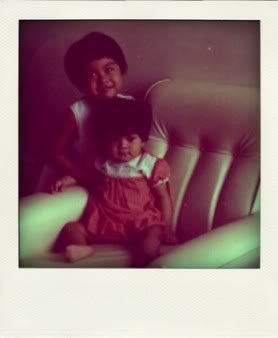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他們,在離島
>>>Wednesday, April 12, 2006
熙來攘往的餐廳裡,我們談論著車子的路線。我問那人你是如何適應市區生活呢?於是他告訴我,舉家如何在他預科那年搬到城市去。遠離那個他成長的離島,除了步伐的急速、人心的複雜,最難以適應的,就是戒掉走到沙灘望海的習慣。喜歡的時候就去看海、踢沙,說來真是一件浪漫的事。他還說起那個小島的居民,總會為外人住進酒店而訕笑──話語中多麼寫意的語調。
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他,其實有點不以為然。面對輕佻的態度,我無法生就好感。但通過幾次偶然的交談,我再次意識到表裡不一的可能──連他也說,某種穿戴,只為了保護自己。那個多小時裡,他還提起虛偽的嘴臉,甚至是日後的志願。如此窩心的萍水相逢,就交換了號碼,並為對話的微溫而感動。如果今日坐在這裡的三個人能夠到那個地方吃一頓飯,會不會延續今日那個小時的美麗?
離開的時候碰上羅生,我便彷彿蜜蜂黏附蜜糖一樣,在他耳邊嗡嗡嗡嗡。是因為我光看著他落單、取食物、拿開水,然後自顧自跟他交代一些生活,於是骨頭就掉在地上嗎?我有時會想起我寫過的一個片段,然而原形其實從來都不是他。
(最初講起一些出版物,他輕輕地提及粗略的觀感。我好奇,問他那天有沒有出席那個場合?他就一臉傲然的說並不喜歡誰和誰。這樣,我就愉快地笑起上來,再沒有遺憾和不快。甫坐下,他問我電影節有沒有看戲,我卻九唔搭八的說近來只喜歡讀書。原來前一晚他看了 Zizek,我就聽他簡介那人的理論。後來不知怎的又拉扯到賈章柯,我繼續聆聽他的看法,而不語。你有沒有看村上春樹的近作,我問;他便以 fed up 來形容對他的感覺。我聽罷當然大呼小叫,提到近來才真正發現他的不可多得。後來我又自嘲自己文盲的程度,對魯迅和張愛玲視若無睹;我嘆息,廿四歲的遲暮,不可一世的他卻竟然反過來安慰我,勸我別急進,又著我翻翻《沉香》輕鬆一下。於是我便提及工作的一點點見聞,說我最討厭那些造作的場合,不能接受對身份過份自覺而變成看不起人的態度。你知我最憎虛偽,我說。然而他教我,自然就是了。又著我,寫吧,最重要還是寫吧。就這樣他邊吃午飯邊跟我不著邊際的聊天,我禁不住嘲笑他八時半教康德,他那口飯便變得難以下嚥。在 staff canteen 裡,我有時尖叫,他便著我冷靜。偶爾會掠過他的咳嗽,我就問他看中醫的情形。事實上是有點不可思議的,然而愉快的程度實在不是我能夠好好記下來。在他面前我實在很蠢。唯一叫尖刻的他感到興趣的,好像只有在昇降機中提到的奇斯洛夫斯基……每次對他胡言亂語後,總為愚昧遲鈍而感到懊惱。他不嫌我神經質,讓我常常在他身邊講無聊的說話,我卻竟然連一丁點他的才智都沾不上。好蠢呀,難為我還自恃小聰明?只有在他跟前。)
在他跟前我突然變得氣短和力弱。他把沉重的門關上,面對面的對話彷彿遙遠而不可即。我戰戰兢兢的問,可以嗎?他也小心翼翼地回答,可以。但我實在討厭這樣的拘謹,我怕我快撐不下去了。
收到那本小冊子的時候還附有一張字條,原來我竟看漏了那流麗的筆跡。說到底,我現在已不懂得處理這樣的關係。當初把一切強行戳穿,今日變節了又要如何申辯?但我想她是懂得的,也因此我更感激別人的落落大方,至少我絕不可能如此得體。我抓狂,又任性。是看錯了。牽涉情感難道就不能趨向簡單一點嗎?我知道她的善良和真誠。我也懂得甲乙丙丁也許都比我懂得如何愛下去。我斤斤計較,不能接受虧欠──其實是不值得愛的。因此,總是相遇又告吹,最後還是學不會。遺棄的聲音又響起了。有時我真的很想對那人說,難道你還感受不到她們的情份嗎?但身處這個位置,我理應懂得恰如其分。
最後還滿足了物質的慾望,我想,我應當是快樂的。
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他,其實有點不以為然。面對輕佻的態度,我無法生就好感。但通過幾次偶然的交談,我再次意識到表裡不一的可能──連他也說,某種穿戴,只為了保護自己。那個多小時裡,他還提起虛偽的嘴臉,甚至是日後的志願。如此窩心的萍水相逢,就交換了號碼,並為對話的微溫而感動。如果今日坐在這裡的三個人能夠到那個地方吃一頓飯,會不會延續今日那個小時的美麗?
離開的時候碰上羅生,我便彷彿蜜蜂黏附蜜糖一樣,在他耳邊嗡嗡嗡嗡。是因為我光看著他落單、取食物、拿開水,然後自顧自跟他交代一些生活,於是骨頭就掉在地上嗎?我有時會想起我寫過的一個片段,然而原形其實從來都不是他。
(最初講起一些出版物,他輕輕地提及粗略的觀感。我好奇,問他那天有沒有出席那個場合?他就一臉傲然的說並不喜歡誰和誰。這樣,我就愉快地笑起上來,再沒有遺憾和不快。甫坐下,他問我電影節有沒有看戲,我卻九唔搭八的說近來只喜歡讀書。原來前一晚他看了 Zizek,我就聽他簡介那人的理論。後來不知怎的又拉扯到賈章柯,我繼續聆聽他的看法,而不語。你有沒有看村上春樹的近作,我問;他便以 fed up 來形容對他的感覺。我聽罷當然大呼小叫,提到近來才真正發現他的不可多得。後來我又自嘲自己文盲的程度,對魯迅和張愛玲視若無睹;我嘆息,廿四歲的遲暮,不可一世的他卻竟然反過來安慰我,勸我別急進,又著我翻翻《沉香》輕鬆一下。於是我便提及工作的一點點見聞,說我最討厭那些造作的場合,不能接受對身份過份自覺而變成看不起人的態度。你知我最憎虛偽,我說。然而他教我,自然就是了。又著我,寫吧,最重要還是寫吧。就這樣他邊吃午飯邊跟我不著邊際的聊天,我禁不住嘲笑他八時半教康德,他那口飯便變得難以下嚥。在 staff canteen 裡,我有時尖叫,他便著我冷靜。偶爾會掠過他的咳嗽,我就問他看中醫的情形。事實上是有點不可思議的,然而愉快的程度實在不是我能夠好好記下來。在他面前我實在很蠢。唯一叫尖刻的他感到興趣的,好像只有在昇降機中提到的奇斯洛夫斯基……每次對他胡言亂語後,總為愚昧遲鈍而感到懊惱。他不嫌我神經質,讓我常常在他身邊講無聊的說話,我卻竟然連一丁點他的才智都沾不上。好蠢呀,難為我還自恃小聰明?只有在他跟前。)
在他跟前我突然變得氣短和力弱。他把沉重的門關上,面對面的對話彷彿遙遠而不可即。我戰戰兢兢的問,可以嗎?他也小心翼翼地回答,可以。但我實在討厭這樣的拘謹,我怕我快撐不下去了。
收到那本小冊子的時候還附有一張字條,原來我竟看漏了那流麗的筆跡。說到底,我現在已不懂得處理這樣的關係。當初把一切強行戳穿,今日變節了又要如何申辯?但我想她是懂得的,也因此我更感激別人的落落大方,至少我絕不可能如此得體。我抓狂,又任性。是看錯了。牽涉情感難道就不能趨向簡單一點嗎?我知道她的善良和真誠。我也懂得甲乙丙丁也許都比我懂得如何愛下去。我斤斤計較,不能接受虧欠──其實是不值得愛的。因此,總是相遇又告吹,最後還是學不會。遺棄的聲音又響起了。有時我真的很想對那人說,難道你還感受不到她們的情份嗎?但身處這個位置,我理應懂得恰如其分。
最後還滿足了物質的慾望,我想,我應當是快樂的。
:: posted by my lock, 4:52 P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