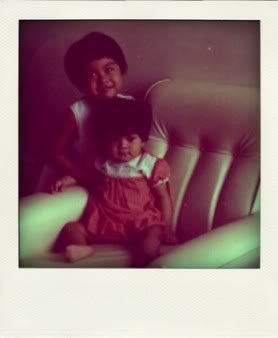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名字的倒刺
>>>Monday, September 04, 2006
路是一個人用一雙腿慢慢走在出來的。繁華盛世,燈光普照,我對街道的迂迴感到莫名陌生。住在新界,小時候來回往還都用一目了然的火車,地鐵在我看來已經縱橫交錯,巴士小巴的複雜叫我驚懼。總是迷路、繞圈子,風景卻依然屬於過眼雲煙。我看過一個倪匡的訪問,他提到在酒家上洗手間後會找不回原來的桌子,像我永遠不能在離開K房以後尋回自己的房間──假設我沒有記住門牌的號碼。
車廂內,我看穿玻璃外的風景,穿越西隧前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房子,讓我倏然落淚的紀念碑。剛跟某位先生掛線,我就忍不住垂淚,我是那麼需要一個庇護,但先生有要事不能見我,我像失去依歸的寄居蟹,只有一團脆弱的嫩肉,暴露在空氣之中,隨時被踐踏與變壞。
我們苦難的馬戲班/夏宇
逐漸熟讀夏宇的詩(然而我懂得多少。我並不。),〈我們苦難的馬戲班〉早被我一次又一次地抄寫。因為名字,我那麼喜愛的名字──只有我喜愛的人,才會被我細細唸他的名字。
我只會喊我所喜歡的人的名字。
安德烈在那時候問我借過筆記,但我拒絕了他,因為我無法給他看見紙張上毛毛細細地抄寫著他的名字。那一課,我們學 ALTHUSSER 與 ideology,還有 David Lynch 的 "Mulholland Dr.",當然我仍記得他做功課的電影是 Tarkovsky 的 "Zerkalo",那齣我其後看了很多次也無法明白的電影。
我相信我們都懷有命名的癖好。像密碼一樣,只有我們才懂得錯不了的按圖索驥,他曾經把玩我的名字,像馬戲班內拋擲鮮橙的小丑。(他,被排拒於我們之外。)但我最後喝了一杯牛奶,我被攪拌,很痛,很痛。
離開的時候,我又瑟縮在火車內,流動的新聞直線,有張宏艷為您報道新聞──阿加斯流下的眼淚、BA 叔的白頭,這些人生的軌跡,都幻化成一束束旁人眼中的電光幻影,只有當事人才懂得真正的跌宕(我的哀傷)。我的名字,w。親愛的存在主義信徒,同理心破滅的社會,我們總是無法打碎一道又一道的牆──我的愛還是不曾被真正了解與珍惜。我還會不會再喊那個人的名字呢?我仍是那個過於煽情的女子,連讀體育新聞都被感染落淚的女子。那樣輕省、廉價、造次,怪不得我就要被嫌棄,只能成為昨日最親的某某。
* 2006/09/12
車廂內,我看穿玻璃外的風景,穿越西隧前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房子,讓我倏然落淚的紀念碑。剛跟某位先生掛線,我就忍不住垂淚,我是那麼需要一個庇護,但先生有要事不能見我,我像失去依歸的寄居蟹,只有一團脆弱的嫩肉,暴露在空氣之中,隨時被踐踏與變壞。
當沒有人知道如何旋轉譬如你
背著海。骰子停止的時候
第幾次永恆又回到偶然 你留下來
你留下來好不好
我們苦難的馬戲班/夏宇
逐漸熟讀夏宇的詩(然而我懂得多少。我並不。),〈我們苦難的馬戲班〉早被我一次又一次地抄寫。因為名字,我那麼喜愛的名字──只有我喜愛的人,才會被我細細唸他的名字。
我只會喊我所喜歡的人的名字。
安德烈在那時候問我借過筆記,但我拒絕了他,因為我無法給他看見紙張上毛毛細細地抄寫著他的名字。那一課,我們學 ALTHUSSER 與 ideology,還有 David Lynch 的 "Mulholland Dr.",當然我仍記得他做功課的電影是 Tarkovsky 的 "Zerkalo",那齣我其後看了很多次也無法明白的電影。
我相信我們都懷有命名的癖好。像密碼一樣,只有我們才懂得錯不了的按圖索驥,他曾經把玩我的名字,像馬戲班內拋擲鮮橙的小丑。(他,被排拒於我們之外。)但我最後喝了一杯牛奶,我被攪拌,很痛,很痛。
離開的時候,我又瑟縮在火車內,流動的新聞直線,有張宏艷為您報道新聞──阿加斯流下的眼淚、BA 叔的白頭,這些人生的軌跡,都幻化成一束束旁人眼中的電光幻影,只有當事人才懂得真正的跌宕(我的哀傷)。我的名字,w。親愛的存在主義信徒,同理心破滅的社會,我們總是無法打碎一道又一道的牆──我的愛還是不曾被真正了解與珍惜。我還會不會再喊那個人的名字呢?我仍是那個過於煽情的女子,連讀體育新聞都被感染落淚的女子。那樣輕省、廉價、造次,怪不得我就要被嫌棄,只能成為昨日最親的某某。
* 2006/09/12
:: posted by my lock, 4:28 P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