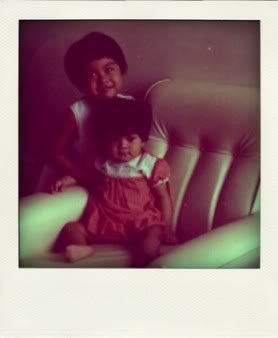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匙.綠色.身份證
>>>Friday, May 26, 2006
1.
有時,希望卑微得叫人不忍看下去吧。然而我還是翻開了地毯,金屬的冰涼傳到我的掌心之中。在糾結的伏線裡,彷彿看到屬於我們的出口。推開門,還有無數的門,但風鈴的叮嚀一直存留在心深處。是的,我不過希望把信交給你,然後,看見你一個真誠的微笑。如果你明白。(或者你不明白只是因為我不夠努力之故。)
2.
K真是一個溫柔男子。他喜歡對著電話的留言信箱說一些叫人感到窩心溫暖的說話。K以為我長期不接電話代表不快樂,甚至會害怕鈴聲過於頻密而叫我感到厭煩。但K並不知道,有時不過因為電話沒有充電,有時不過因為我的生理周期再次循環而缺乏說笑的動力。K還以為上星期四的痛殘留在我身體裡,事實我的心血為另一個人而白流──但畢竟我還沒有死。我太好命了。
實際上我為K而感到擔心不已,於是在我拒絕聆聽K來電之同時,我打了電話給L。我知道,我那些過於急速的說話節奏叫L感到事情的急迫性,事實上我甚至從不為自己這樣勇猛爭取,我卻為了K的前途而盡心盡力。
 無論K是否一名溫柔男子,但K是給我介紹 Belle and Sebastian 的人。那張他借我的唱片,綠色封面的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依舊清新雋永。
無論K是否一名溫柔男子,但K是給我介紹 Belle and Sebastian 的人。那張他借我的唱片,綠色封面的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依舊清新雋永。
3.
屬於我那個換證階段的最後一天。晚上八時半,我到達入境處,依循一般程序辦手續。大概因為我有點高低膊大細面,相片總是拍不好,歪歪斜斜的,結果影了五六張才好勉強了事,連那女職員都覺得有點煩厭。我安慰自己日後的落差也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罷了。等候的瞬間留意到女職員座位上用來放文具的筆座與小盒子,竟然貼有幾塊杜魯福的大頭照──就是很原始的以彩色打印機把喜歡的小頭像列印出來,然後像做勞作一樣,剪剪貼貼──我驚訝得很,於是周圍張望看看鄰座的職員是否也如此雅緻。杜魯福幾時變成公營機構的法定肖像?最後卻還是禁不了好奇向那中年女職員發問,那是杜魯福嗎?結果我們不合程序地談了分零兩分鐘杜魯福的電影。那算是一種驚喜嗎?我只留意到,原來用了網上預約的我是毋須再填寫生日日期的。
有時,希望卑微得叫人不忍看下去吧。然而我還是翻開了地毯,金屬的冰涼傳到我的掌心之中。在糾結的伏線裡,彷彿看到屬於我們的出口。推開門,還有無數的門,但風鈴的叮嚀一直存留在心深處。是的,我不過希望把信交給你,然後,看見你一個真誠的微笑。如果你明白。(或者你不明白只是因為我不夠努力之故。)
2.
K真是一個溫柔男子。他喜歡對著電話的留言信箱說一些叫人感到窩心溫暖的說話。K以為我長期不接電話代表不快樂,甚至會害怕鈴聲過於頻密而叫我感到厭煩。但K並不知道,有時不過因為電話沒有充電,有時不過因為我的生理周期再次循環而缺乏說笑的動力。K還以為上星期四的痛殘留在我身體裡,事實我的心血為另一個人而白流──但畢竟我還沒有死。我太好命了。
實際上我為K而感到擔心不已,於是在我拒絕聆聽K來電之同時,我打了電話給L。我知道,我那些過於急速的說話節奏叫L感到事情的急迫性,事實上我甚至從不為自己這樣勇猛爭取,我卻為了K的前途而盡心盡力。
 無論K是否一名溫柔男子,但K是給我介紹 Belle and Sebastian 的人。那張他借我的唱片,綠色封面的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依舊清新雋永。
無論K是否一名溫柔男子,但K是給我介紹 Belle and Sebastian 的人。那張他借我的唱片,綠色封面的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依舊清新雋永。3.
屬於我那個換證階段的最後一天。晚上八時半,我到達入境處,依循一般程序辦手續。大概因為我有點高低膊大細面,相片總是拍不好,歪歪斜斜的,結果影了五六張才好勉強了事,連那女職員都覺得有點煩厭。我安慰自己日後的落差也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罷了。等候的瞬間留意到女職員座位上用來放文具的筆座與小盒子,竟然貼有幾塊杜魯福的大頭照──就是很原始的以彩色打印機把喜歡的小頭像列印出來,然後像做勞作一樣,剪剪貼貼──我驚訝得很,於是周圍張望看看鄰座的職員是否也如此雅緻。杜魯福幾時變成公營機構的法定肖像?最後卻還是禁不了好奇向那中年女職員發問,那是杜魯福嗎?結果我們不合程序地談了分零兩分鐘杜魯福的電影。那算是一種驚喜嗎?我只留意到,原來用了網上預約的我是毋須再填寫生日日期的。
:: posted by my lock, 7:42 A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