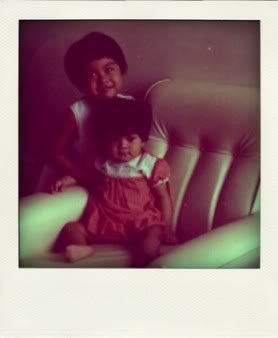* 寫字無用
>>>Sunday, January 22, 2006
因為修過小說課,好好歹歹也寫過三個短篇。除了替我批改的陳老師及親愛的羅生讀過以外,我一直只期望那個人看一看,讓他知道我也不是那末糟糕,至少還懂得寫字。重看也心知小說內容很爛,除了我的文筆的確相當不錯之外;即使我又不容否認,那是一種花拳繡腿。無論如何,重要的是那個人讀了,尤其我最鍾愛的最後一篇﹕〈夏〉。唉,不知道他以為小說中方先生的原型是誰呢。
 大四那年,修了新詩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三個月內終於寫了四首。又彷彿毒癮一樣,大部份都關於那個人,縱然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懷疑那個人到底是否懂得方塊字的好處。有次念及這點,心血來潮就寫了〈不是安德烈與瑪格烈特〉,譯名的挪用並非刻意陌生化,一切純粹為了那人。因此知道《依莎貝拉》,也是挺高興的。為甚麼譯名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祖與占。去年二月底,但見眉目的時候,又寫了另外一首。可是,錯在改壞名,結果真的一語成懺──小朋友的說話,作不了準。
大四那年,修了新詩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三個月內終於寫了四首。又彷彿毒癮一樣,大部份都關於那個人,縱然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懷疑那個人到底是否懂得方塊字的好處。有次念及這點,心血來潮就寫了〈不是安德烈與瑪格烈特〉,譯名的挪用並非刻意陌生化,一切純粹為了那人。因此知道《依莎貝拉》,也是挺高興的。為甚麼譯名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祖與占。去年二月底,但見眉目的時候,又寫了另外一首。可是,錯在改壞名,結果真的一語成懺──小朋友的說話,作不了準。
到底有甚麼能夠推動像我這樣懶惰的一個女子去寫呢?唉,可恨我目光如豆。當愛情沒有流動,生活中只剩下工作工作和工作(正職兼職與補習,我還奢望分身去教琴),身體早已頹敗,一天到晚只想不做夢睡爛覺(發夢真是會耗費氣力的)。沉重工作磨蝕早已薄得可憐的意志,連夢都不願做,我哪裡還有氣力去破冰?
寫作貼近戀愛大概都與激情有關。癢的時候就特別喜歡寫,心裡像擱有千言萬語無法不表達,猶如一群亂竄的螞蟻,企圖找尋最後的洞穴。尤其當文字被書寫在青綠色的原稿紙上,一隻隻一格格,到底也是種鎮靜心神的方式。因此,礙於天資不足,縱然寫得不好,我也願意寫。
小說與新詩及後得到嘉許,自然是始料不及的。因為得獎而衍生的另一個故事,更加無心插柳。寫的時候說是為了那人,真正感動的卻是自己。也許還另外感動過在我們以外的一些人,但說穿了滿足的不又是自己。愛情其實都是一樣的,再愛也是自己。原來原型都不過是自己自己與自己,真是悶。縱然今日我還是嗅到一陣薄荷的清新氣息,縱然我明白一切的關聯感應,縱然我清楚帷幕背後的千瘡百孔,然而,到底也是為了自己自己與自己,一種更深的毒癮。
是如何從甲點走到戊點的呢?我只是比較敏感,到底也是僅此而已。而我其實從不認路,從不。也因此我經常迷路──究其到底,原來我是不值得信任的。
 大四那年,修了新詩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三個月內終於寫了四首。又彷彿毒癮一樣,大部份都關於那個人,縱然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懷疑那個人到底是否懂得方塊字的好處。有次念及這點,心血來潮就寫了〈不是安德烈與瑪格烈特〉,譯名的挪用並非刻意陌生化,一切純粹為了那人。因此知道《依莎貝拉》,也是挺高興的。為甚麼譯名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祖與占。去年二月底,但見眉目的時候,又寫了另外一首。可是,錯在改壞名,結果真的一語成懺──小朋友的說話,作不了準。
大四那年,修了新詩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三個月內終於寫了四首。又彷彿毒癮一樣,大部份都關於那個人,縱然直至今時今日我仍然懷疑那個人到底是否懂得方塊字的好處。有次念及這點,心血來潮就寫了〈不是安德烈與瑪格烈特〉,譯名的挪用並非刻意陌生化,一切純粹為了那人。因此知道《依莎貝拉》,也是挺高興的。為甚麼譯名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祖與占。去年二月底,但見眉目的時候,又寫了另外一首。可是,錯在改壞名,結果真的一語成懺──小朋友的說話,作不了準。到底有甚麼能夠推動像我這樣懶惰的一個女子去寫呢?唉,可恨我目光如豆。當愛情沒有流動,生活中只剩下工作工作和工作(正職兼職與補習,我還奢望分身去教琴),身體早已頹敗,一天到晚只想不做夢睡爛覺(發夢真是會耗費氣力的)。沉重工作磨蝕早已薄得可憐的意志,連夢都不願做,我哪裡還有氣力去破冰?
寫作貼近戀愛大概都與激情有關。癢的時候就特別喜歡寫,心裡像擱有千言萬語無法不表達,猶如一群亂竄的螞蟻,企圖找尋最後的洞穴。尤其當文字被書寫在青綠色的原稿紙上,一隻隻一格格,到底也是種鎮靜心神的方式。因此,礙於天資不足,縱然寫得不好,我也願意寫。
小說與新詩及後得到嘉許,自然是始料不及的。因為得獎而衍生的另一個故事,更加無心插柳。寫的時候說是為了那人,真正感動的卻是自己。也許還另外感動過在我們以外的一些人,但說穿了滿足的不又是自己。愛情其實都是一樣的,再愛也是自己。原來原型都不過是自己自己與自己,真是悶。縱然今日我還是嗅到一陣薄荷的清新氣息,縱然我明白一切的關聯感應,縱然我清楚帷幕背後的千瘡百孔,然而,到底也是為了自己自己與自己,一種更深的毒癮。
是如何從甲點走到戊點的呢?我只是比較敏感,到底也是僅此而已。而我其實從不認路,從不。也因此我經常迷路──究其到底,原來我是不值得信任的。
:: posted by my lock, 6:01 AM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
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牆上鴨屎綠的油漆逐漸剝落,斑駁得像一個個流離失所的孤島。擁有房子,仍在漂流。是生活,是創作。其實我們都是房子。有時是門鎖,有時是鑰匙。幸而這裡盛載記憶,archive 作為刻度的提示。至於綠色,是我們叩門時的三長兩短。咯咯,這是一所綠色的房子。